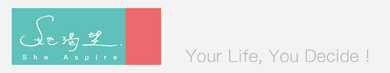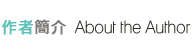有共融式樂園,才有共同的童年/ 余秀芷sleeve
下課鈴聲一響,跟朋友直衝操場,我們約好要去搶那個用鐵條架構起的地球儀,有時候是大象溜滑梯,有時候是操場上的躲避球大賽,這是國小時候的下課十分鐘。
那時候,我可以用自己的雙腳奔跑,要能爬上地球儀或者溜滑梯,一點都不需遲疑、沒有任何阻礙,我跟同學盡情地奔跑,他們喜歡在地球儀裡面找個地方坐下,在地球儀外圍的我,則是拉著地球儀的邊條,開始順著一個方向推動,由吃力地推動,到快速地奔跑,享受著轉動時的速度感,也享受著因速度揚起的風,我們一起旋轉,一起開心地尖叫著,這畫面到現在還是十分清晰。
上課鐘聲響,我們會一起發出掃興的哀嚎聲:「哎唷~」,印象中,準備奔回教室的路途,我常會在大象溜滑梯的下方,或是操場旁的花圃邊,見到我們班的一個障礙生,他因為成骨不全症,校園許多好玩的遊樂器材都無法使用,他最常跟班上幾個女孩子,躲在大象溜滑梯下的小空間裡,一起看書,或者說著小女生內心的秘密,有幾次我會問她要不要一起玩盪鞦韆,我可以在後面幫她堆鞦韆,或者刺激的蹺蹺板,我保證一定會輕輕地,不像平常時候玩得那麼暴力,但她總是微笑地搖搖頭:「我不想玩」。
到長大後才知道,這些都是他無法玩的遊戲,不是因為她身體的關係,而是因為這些遊樂器材,並沒有適合他的設計,在他的心中或許是很想加入我們,跟我們一起在下課時間享受速度感,盡情瘋狂的尖叫。
長大後的現在,自己成了障礙者,回想起這一段記憶,回想這位同班的女同學,他的童年因為環境的缺乏,失去了某一塊每個人最通常的快樂回憶。而我,似乎面對的是另一種記憶的遺憾…
隨著小外甥們慢慢長大,我在公園與遊樂場中,只能跟其他年長的老人家們待在外圍,看著小外甥們遊玩,當他們上前詢問我可不可以陪他們一起玩時,我卻只能滿心抱歉的對他們說:「輪椅無法玩那個。」我開始明白到當年那位同學心中的惆悵,那微笑著說不想玩,其實卻是「我很想玩,但無法玩。」小外甥們比當年的我更加機靈,更有障礙意識,當我只能在旁邊看著,他們總是氣憤地說:「應該要有秀芷阿姨可以一起玩的設計啊,這樣子很不公平。」接著天馬行空的開始說出什麼樣的設計就可以讓我們一起玩了。
這讓我想起最近當媽媽的障礙姐妹們,有一次藉著採訪,我問女兒剛滿兩歲的舒帆,當他帶著女兒去公園或者親子餐廳,怎麼陪著孩子一起遊戲?舒帆跟我說,如果老公沒空一起出門,他總是請女兒自己去玩,遠遠的看著他女兒,只能用眼神守護著她,小女孩總是會有撒嬌的時候,當女兒用期盼的眼神看著舒帆說:「媽媽陪我玩溜滑梯。」舒帆也只能告訴他:「媽媽的輪椅無法爬上去,你自己玩。」而當孩子在遊戲區摔倒了,也只能依靠在遊戲區裡的其他大人們協助,舒帆無奈的說:「沒辦法,在這樣的環境下,我的女兒只能提早學會獨立。」當然這是在台灣的處境,舒帆遠嫁到日本去,回到日本的他們,會一起去幾個有共融遊樂器材的公園遊戲,舒帆可以陪著女兒爬上溜滑梯,也可以一起玩鞦韆。
小時候的下課十分鐘,到長大後的現在,我經歷障礙者與非障礙者的生活方式,但感受最深的,是那種不能一起玩的失落,過去失落於無法與同班的障礙生一起玩,現在失落於無法跟小外甥們一起玩,而相同的狀況是,在環境方面,我們還沒有共融式的遊樂設施,在情感部分,如果環境沒有共融式的設計概念,我們終究都要去經歷這樣的失落感。
如果您也想關注共融式樂園議題,請到「共融遊樂」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RightToPlayTaiwan/?fref=ts
  |
 「遇見美麗的自己」活動花絮與感謝
「遇見美麗的自己」活動花絮與感謝2015年9月5號,匯聚眾善力量與祝福的「遇見美麗的自己」公益彩妝教學正式開始囉!這是台灣非常少見以彩妝教學為主的公益活動,活動中共有50位特殊境遇婦女參與,重新遇見了美麗的自己!
 余秀芷專欄-納美人與她的迅雷翼獸
余秀芷專欄-納美人與她的迅雷翼獸突然覺得自己好像電影阿凡達裡的納美人,電動輪椅就是迅雷翼獸,將右手擺在遙控桿上,如同納美人與迅雷翼獸的觸角相連,將電動輪椅馴服,與他合而為一,就可以自在的悠遊於這空間中了。